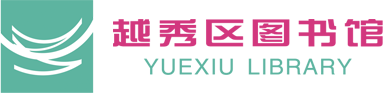11月19日,由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越秀区图书馆承办的“广府新语”(87期)讲座《广东音乐传承与发展》在新花城APP顺利播出,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本期讲座由星海音乐学院吴迪副教授主讲,并特邀广东新快报社广州新闻部首席记者邓毅富担任主持人,与嘉宾对谈。
据吴教授介绍,广东音乐有信史可考的发展历史约有200年。广东音乐是在珠江三角洲慢慢发展起来的,广州是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区域。“广东音乐”是一个后来才流行起来的词汇,最早被称为“粤乐”。从行业发展、文化交流等因素综合看,粤剧、粤曲、粤乐都是无法分割的,所以学界有“三粤合一”的说法。从19世纪中叶开始,广东音乐出现了,但具体年份节点无法确知。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广东音乐的发展更多地处于民间状态。道光、咸丰年间,广东音乐快速发展,文人参与广东音乐创作,对广东音乐进行了提升。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广东音乐作品的作者都是有名有姓的,大量作者参与广东音乐作品的创作,对广东音乐成为一个显化的乐种作出了贡献。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广州“一口通商”的时代结束,上海开埠,一批广东人到上海经商,广东音乐随之传播到上海,慢慢地,广东音乐的传播遍布全国。百年前,广东音乐已发展成一个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乐种。
对谈中,邓记者问到了广东音乐曲目的源流。吴教授介绍,广东音乐当中的《昭君怨》《妆台秋思》这种曲目,来自于中原古乐。琵琶曲的作品,比如《塞上曲》,被本土化之后,有了“粤化”的痕迹,成为经典的广东音乐曲目。但上述曲目只是广东音乐当中的一部分,广东音乐更多的曲目是有名有姓的创作,这个阶段从什么时候开始呢?那就要从广东沙湾何氏家族的何博众这一位人物开始讲起,他是一位标志性的人物。广东音乐历史上,有两位名人,被称为奠基人,他们对广东音乐的形成具有关键作用:一位是何博众,一位是严老烈。
南宋绍定六年(1233年),因世乱放弃仕途的何德明从广州清水濠迁居番禺沙湾,成为后来财雄势大的沙湾何氏宗族始祖。仓廪丰足造就了何氏家族的音乐文化,音乐成了何氏家族的精神食粮。何氏出了数位广东音乐名家,何博众(1833~未详)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位。
传说何博众的琵琶很厉害,被称为“十指琵琶”“十指琵琶王”。现在的琵琶演奏家演奏的时候,基本十个手指都会用到。但是,清代的琵琶分南派、北派。北派琵琶的演奏基本十个手指都会用到,但是广东地区民众在那个年代不太经常见到“十指琵琶”的演奏技艺,当时交通、信息也比较闭塞,于是大家开始称何博众为“十指琵琶王”。何博众创作了一些很著名的作品,但是在当时的文人观念中,创作是要托古的。所以,现在学界一般认为《饿马摇铃》等广东音乐曲目是何博众传谱的,是不是何博众创作的,没有定论,但肯定与沙湾何氏家族脱不了干系。
何氏家族的何柳堂、何少霞、何与年也都对广东音乐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被称为“何氏三杰”。

据吴教授介绍,广东音乐,可雅可俗,可盐可甜。大家形容沙湾何氏音乐风格会用“典雅”这个词,但是,广东音乐《赛龙夺锦》反映的是民俗活动,有世俗生活的浓厚成分,这是所谓“俗”的一面;但是,没有一定水平的艺术感悟,是创作不出《赛龙夺锦》这样的作品的,这是“雅”的一面。又比如《饿马摇铃》,中国从来没有同名题材的民间音乐,其曲目创意来源于“悬羊击鼓、饿马摇铃”的典故:宋代,抗金名将毕再遇和金兵守垒对抗,金兵强大,宋营兵少,毕再遇便在一个夜里把队伍全部撤走,只留旗帜在阵地上,把铃铛吊在饿马蹄子上发出声音。金兵听到马嘶、铃声,没起疑心,也不敢进攻,等了几天,才发觉中计,这就是“饿马摇铃”的典故。所以,广东音乐《饿马摇铃》的旋律也是摇摆的。如果没有文化积累,是不会想到用典故来作为曲目名称的。又比如《醉翁捞月》,题目是古画常见的题材。何与年的《小苑春回》《午夜遥闻铁马声》,题目都很雅致,这里的“铁马”,是古建筑屋檐上的风铃,也是一个很雅致的意象。
再说回严老烈。相比沙湾何氏音乐的乡绅风格,严老烈是完全不同的风格。比如《连环扣》,有人说它是中国的《无穷动》,清代中国民间音乐当中很少见到节奏这么快的音乐。而《连环扣》居然是从民间音乐《寡妇诉怨》改编过来的,《寡妇诉怨》旋律很慢,传达的情绪比较消极,却被严老烈改成了一首在清代惊世骇俗的曲子。又比如《旱天雷》,有人认为它是号召革命的曲目。19世纪的中国,民间涌动着革命的情绪,广东更是成为了辛亥革命的策源地,《旱天雷》在那个时代诞生了,它多少流露了民间对于变革的呼唤。
吴教授分享道,我们还应该提起一个很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人物——丘鹤俦,是他整理出版了《弦歌必读》这本著作,在这之前,很少有记录广东音乐的文献。《弦歌必读》当中有关于广东音乐的观念陈述,有对广东音乐本身的描述,有曲集,还会用文字告诉你如何用乐器演奏这个曲子,是功能性很完备的文本,往后不断再版,在市场上流传着不同的版本。丘鹤俦是广东台山端芬镇人,他用半文言文的方式去写书,文本内容反映了他深厚的文化积淀。他的形象,是那个年代的岭南人形象的一个缩影和代表:曾经接受西式的教育,受西方影响,知识结构中又保留着传统文化的成分。《弦歌必读》奠定了广东音乐理论研究的基础,其出版也是中国民间音乐理论研究历史上很重要的节点。当时的广东音乐,连唱片都没有出现,《弦歌必读》的存在,深刻影响了民国五年后的广东音乐。广东音乐终于有了乐谱文本,让更多的人可以凭借文献去学习乐谱。广东音乐不是家族秘传,也不是师带徒、口口相授,更多地是利用乐谱文本、唱片这些公开传播的载体。

(丘鹤俦先生资料照片)
1910年代末,上海出现一位标志性的人物——吕文成,他被后人誉为“粤乐泰斗”“一代宗师”。三岁,他跟随父亲去上海谋生,开饼店,也当过首饰店的学徒,读过小学,对参加社会性的音乐活动很感兴趣。他频频出没在乐社、京剧社团等。当时的上海华洋杂处,吕文成在青少年阶段接受了大量音乐熏陶,扬琴弹得非常好,二胡也不错。他是一位天才音乐家,执着追求创新。
20世纪20年代中期,旅居上海的吕文成先生根据江南二胡进行改革制出高胡,被人们称为广东音乐的“灵魂乐器”。而提到高胡发明,就不得不提到司徒梦岩先生。司徒梦岩先生在吕文成先生改制高胡的过程中,可谓是起着重要的作用。

(吕文成先生资料照片)
吕文成先生曾跟随司徒梦岩先生学习演奏小提琴,二人在交流琴艺、探讨音乐过程中,发现此时粤乐中所用的江南二胡音量小、噪音多,师徒二人深感江南二胡的不足,便开始了现今粤乐主奏乐器高胡的研制。司徒梦岩先生精于小提琴制作,对乐器的制作、用料等都具有丰富的知识与经验。经乐器制作师(也是造船专家)司徒梦岩与乐器演奏家吕文成二人的反复研究,高胡最终成功降世。高胡的声音有点像小提琴,但是演奏技巧具有广东音乐的显著特征,被称为广东音乐的“灵魂乐器”。

(司徒梦岩先生资料照片)
当时上海的闸北、虹口是广东人聚居的地方,被称为“小广东”,广东人在上海的工商界执牛耳。广东人由此在上海获得大量工作机会,居住在上海的广东人的生活风尚,影响了上海本地的生活风尚。吕文成在这样的氛围中发展,越来越成功,很有影响力。他把高胡拉出了生命,拉出了灵魂。他创作的作品,留在世上的有200多首。现在流行的广东音乐曲目有500多首,他一个人占了将近一半。也有专家认为,广东音乐曲目有1000多首,但是,其中普遍流行的是500多首。据不完全统计,各大唱片公司所灌录的唱片,由他演奏和演唱的乐曲和粤曲,就有270多张,每张都是卖断货的。
吴教授还提到,“粤乐”,广东人喜欢在某些场合用这个词汇。“广东音乐”则是一个适合于传播的词语。以前的黑胶唱片有小圆孔,上面会有贴纸,小孔上面写“广东音乐”,下面写“名家灌录”,本来这八个字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小孔的存在,被分开了,慢慢地,“广东音乐”这个词语就传开了,后来又影响到广东本地,进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也是“广东音乐”这个词。现在“粤乐”和“广东音乐”两个词语都同时在用,体现了岭南文化的包容性。
邓记者向吴教授请教了广东音乐的乐器。吴教授指出,广东音乐被认为是丝竹音乐,但其实广东音乐乐器不是只有丝竹乐器,不是只有五架头。1925年没有高胡之前,广东音乐演奏的乐器组合是硬弓的五架头,香港人叫它们“硬嘢”。“硬”这个词是核心,弹出来的声音也是硬邦邦的,颗粒很清楚。以前没有麦克风,所以弹奏音乐一定要很大声,乐器张力比较大。所以,五架头只是广东音乐一个比较典型的符号代表。后来有了麦克风,就出现了软弓组合。
说到广东音乐的魅力与传播,吴教授分享了自己观察到的现象:但凡中国的民族音乐乐团出国演出,曲目一定有广东音乐,海外的广东人很多,他们喜欢听乡音。潮汕人、客家人也是广东人,吴教授到客家地区做音乐考察,在当地汉乐八音班休息的时候,吴教授就问他们会不会弹奏广东音乐,结果他们都会,人人都会。很多广东音乐作品洋溢着岭南人热气腾腾的烟火世俗生活气息;另一方面,广东音乐还有很多雅俗共赏的作品、具有文人气质的作品,依然在长期公开演奏。从吕文成那个时代开始,广东的音乐家们开始在上海传播广东音乐。1931年淞沪会战后,一批广东的音乐家去了香港,广东音乐在香港得以广泛传播,上海和香港成为广东音乐发展的重要的“双城记”,广东音乐由此走向四面八方,走向世界。像类似于“广东音乐联谊会”这样的民间社团最早是在北京成立的。天津、东北、兰州……乃至海外,都有不少广东音乐爱好者。
吴迪副教授认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风格,广东音乐也随着时代在发展。广东音乐是多元文化的象征,从早期的传统田园风光,到士绅风格,到后来吸收好莱坞音乐、爵士乐元素,到借鉴西方作曲手法,不断在发展。“声音,具有一个城市代表性的气质。广东音乐很潮,很多元,雅俗共赏,受到公众广泛喜爱。”吴教授说。“是的,广东音乐很潮,有一种引领性的作用,用声音这种特殊的艺术方式走进广东人的生活,在音乐的层面推动着广东文化的发展。吴教授的讲座明白、生动、有观点,很多地方有很生动的描述,非常全面,受益良多。”邓记者也总结性地分享了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