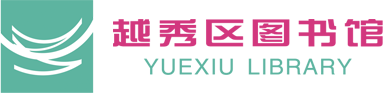孙仁歌:安徽新华学院教授,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带头人,文艺学研究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写作学会第九届理事会理事、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评审专家库专家委员。
诗集《小洲启示录》序言
(孙仁歌)
守住半亩方塘,也终需一员健将。
方塘的真实姓名叫解建,是淮南师范学院2002级中文系学生,毕业转眼间10多年了。时光的确犹如一支激锐的响箭,哧地一声穿越,就让岁月纷纷落地。
大一那年下学期,我给解建那个班主讲了一个学期《现代写作》课程。印象中的解建总是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听课认真,神情专注,一副憨厚、谦卑的状态,始终给老师一种踏实感。课下,解建作为学校飞天文学社的主力成员,为了打造文学的家园,很卖力,也很见才干,尤其连续3年担任社刊《守望者》总编辑的日子里,既把刊物办得不错,也没有影响学业的优异。毕业后,毅然决然直奔广州打拼,历经风雨,也见彩虹。一转眼,“三年的媳妇”也算熬成了“婆”。如今的解建已在广州大都市站稳了脚跟,成家立业,广州显然已经成为他精神世界的“半亩方塘”。
收到这本《小洲启示录》打印稿时,我还不禁为之一惊。印象中,解建一直钟情于小说写作,如今转而为诗,这是一个不小的“自我超越”。文学现象中,不少为诗者常常一个悠然地转身继而成为一个叙事的高手,可圈可点者多多;而由小说转入诗歌并一举跃上葱茏的高手,可举者寥寥。无疑,在广州奋斗的这些年里,大世面大体验,一定给解建留下了许许多多刻骨铭心的经历与记忆,情感世界里不断发生一些碰撞、裂变乃至爆炸,尤其遭遇了小洲村的人文冲击,让作者的灵魂又一次开窍并豁然开朗。一旦气平神宁,魂就沉了下来,俨然天鹅扑水,会溅起无数漂亮的水花。
作者有幸直面小洲村的“蓝天绿海”,又重新燃起了他满怀乡土风景里的“麦秸垛”,以致激情如炽,诗兴勃发,真乃在“有心栽花花不发”之际,却“无意插柳柳成荫”。这或许就是人生的哲学,就是人生的机缘。人的命运有时也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时不时也被一种机缘和巧合所左右。如果不是与小洲村一次巧合的相遇,《小洲启示录》就不会无中生有,从天而降。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美术馆没有落成,我却写了这本诗集,命运的阴差阳错,常让人惊掉下巴。”或许,这诗魂归来的意义远比一个美术馆的落成更有价值!解建终究来自于乡土,内心世界里就储存着一个乡土王国,不经意中与小洲村的一次意外碰撞,激活了他内在世界的全部能源,用诗的形式去开发这样一个属于自己的“理想国”,没准正是成就他寻找文学家园的最便捷的途径。
开诚布公地说,《小洲启示录》很接地气。诗与作者虽不能划等号,但似乎可以说,《小洲启示录》就是解建的文化符号。虽置身于大都市,却心怀乡土,对于曾经生他养他的乡村恩典,已经成为他为诗为文不可或缺的“母题”。解建追求的诗风很本色、很质朴、很笃实,不花哨、不矫情、不玩技,俨然乡土中生产的五谷杂粮,很自然地生长在那里,又呈示出一种“天地合一”的外在风姿。看上去很美,内在的根也扎得很深。
初读《小洲启示录》,又不禁联想起海子的“麦子意象”,台湾陈冠学笔下的“田园之秋”,刘亮程笔下的“乡村哲学”等等,尽管以解建目前的这本诗集还不能与以上诸君相提并论,但从解建写诗的潜力,迟早也会在自己的笔下形成一个定格的乡土意象,从而成为文学圈津津乐道的话题。无论中国社会如何都市化、城市化,也无论中国社会如何工业化、现代化,乡土文学乃至乡土文化都将是中国社会肌体里的灵魂。有关乡土的诗、散文、小说等等之作,仍是新时代文学史上的一道大菜。所以从事乡土题材的写作,前程依然无量,完全不必打折扣。
我就很欣赏《小洲启示录》中的几个选题与命名,诸如第一辑“一个村庄的精神标本”、第二辑“忘了晨昏朝夕的日子”、第三辑“穿过那条时光的河流”、第四辑“我想做一些简单的事情”等等,每一辑中都有惊艳、都有出彩点。偌大一个乡土世界,都被作者浓缩在自我的体悟与思考之中,凝聚成了一首又一首“长笛短管”,构成了一组乡村生态拼图,颇耐人寻味,启示良多。与其说“地球像一个鸭蛋/蛋黄装满火焰”(《小洲启示录》),还不如说“乡村就是装满火焰的蛋黄,激情燃烧的每一个瞬间都饱享蛋黄的营养。”
解建其人其诗,都不乏人文情怀。诗集取材虽杂,却杂而有致,从人情世故到各种小动物、植物、景物以及农作物种种,都在作者的笔下传递出人文主题,尤其氤氲在笔端的悲悯情怀,更具有感人的力量!
如《幸福的眼泪无动于衷》《夜睡了,雪落在故乡的怀里》《祖父的酒祖母的泪》《一棵哭泣的树》《八月的葬礼》《一棵离群的树》《伤痕》《母亲》《按住伤口对世界微笑》等等,都包含人文情怀,诗句内涵更具有耐人寻味的张力。
纵观古今中外文学史上不断沉淀下来的文学现象,凡是那种悲悯情怀厚重的作品,其艺术价值都很好。笔者可能就受这种审美定式及其阅读习惯的渗透,在阅读欣赏各类文学作品中,常常取悲悯为上,或许就中了别林斯基的“邪”:“在诗人的哀愁中认出自己的哀愁,在诗人的灵魂中认出自己的灵魂。”又如朱光潜所说:“悲剧向来被认为是最高的文学形式,取得杰出成就的悲剧家也是人间最伟大的天才。”悲悯自然就不能拒绝悲情乃至悲剧。无疑,正处于人生黄金阶段的解建之于文学审美,不经意中追求的诗艺境界,就不乏悲剧美学的含量。从这本《小洲启示录》所选入的取材多样、情感维度多变的诗作可见,解建更投入的正是对悲情乡土的眷恋、对含泪的“半亩方塘”的皈依,那里才是他灵魂的栖息地,才是他魂牵梦萦的精神故乡。面对这样一个属于自己命中铸魂的世界,种种发现与情思迸发出一首首诗歌作品的时候,他虽然不刻意于一味悲情的表达方式,而是集喜怒哀乐于一体,随兴而生,趣点多多,往往又避“大”趋“小”,以小见大,如此方显“半亩方塘”本色。当然,诗集的整个基调,还是多了些淡淡的忧伤。
解建如今虽置身他乡,却一直挚爱着自己的家乡:“我见过很多地方的池塘/没有一处像我的故乡/故乡的池塘/在房屋的前面/泪眼汪汪闪着波光……”(《故乡的池塘》)作者的忧伤似乎很理性,也很节制,却敞亮而不遮掩。从对一棵倒在路旁的树的感触,也从中可见作者的人文思考:“午夜的梦里/我听见的满树的叶子/在寒冷的风中/放声哭泣/惊心动魄”(《一棵哭泣的树》),从作者对这棵倒地的树的悲悯中,似乎也让我们从中窥视到某个人的影子,人生如树,树如人生,有时候生活就是这样充满了暗示性。
对亲情、乡情、爱情、友情的诗意表达,作者都显得那么从容淡定,那么质朴无华。既不讲究浓妆艳抹,也不讲究花俏惊艳,看似漫不经心,实际上却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尤其对自己最爱的人的诗意表达,也是妙笔生情却未必妙笔生花。“我想在五月的麦芒上/写一首关于母亲的诗/那些皮肤扎满荆棘的记忆/在岁月的深处/变得粗粝并且混沌……/母亲老了/生锈的镰刀卖给了/破烂王老李/她养的那些猪和羊/还有会唱歌的公鸡/全伺候了别人家的餐具……”(《母亲》)不需要卒读全诗,读者就不难体悟到作者对母亲的深切怀念。无疑,母爱于他就像一条穿过时光的河流,会永远在生命的深谷中汩汩流淌。
说千道万,这一切诗意情感的迸发,还在于小洲村的碰撞与开启,所以诗集的点题之作《小洲启示录》就更为耐人寻思:“我知道了/世界并不大/我们的幸福和疾苦/大不过一条瀛水河/我们的欲望和天真/逃不过一座小洲村……”(《小洲启示录》)好一个“逃不过”,或许小洲村就成为解建从此打开世界一扇又一扇神秘之门的钥匙,伴随着自己的梦想,去纵情飞翔。说白了,就是一句话,以诗的形式把自己的灵魂还给乡土。是啊,灵魂来自于乡土,最终还要回归于乡土。或许这就是“逃不过”的魅力所在吧。
限于篇幅,对诗集《小洲启示录》不能展开赏析,只能蜻蜓点水,挂一漏万。作为曾经的老师,笔者也不妨坦言,写诗的路,对于解建来说还很长很长。说实话,诗是不好养的。美学家朱光潜早就告诫一些青年诗人,诗是所有文体中最难侍弄的文体,缺乏精妙的观感和精妙的语言,是很难写出好诗的。解建好在还很年轻,也很有文学天赋,尤其很理性、很内敛,再加上他的勤奋与韧性,或许能突破朱光潜所说的那个坎,迟早会写出那种朱光潜诗学所界定的好诗,扬名诗坛,从而让淮南师范学院引以为荣,让我这个曾经做过他老师的长者引以为自豪!
我们翘首期待,希望解建真的能成为守望“半亩方塘”的一员健将。
2020年1月16日写于忘知斋
资料来源:方塘诗意公众号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本文已获授权发布,未经同意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