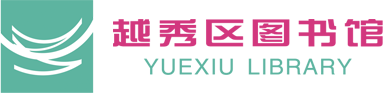正如本期讲座的标题一样,黄海妍馆长为广大听众详尽地介绍了18-19世纪广州手工艺的方方面面。为什么广州的手工艺行业会如此兴盛?那就不得不提广州在世界贸易交流方面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

据黄海妍馆长介绍,从秦汉时期开始,广州就以一个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城市著称,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地理枢纽,同时也是岭南地区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明代以后,以广州为中心的海外贸易发生了改变,由以周边国家的朝贡贸易为主转变为对西方国家进行出口贸易为主。朝贡贸易亦称“随贡贸易”、“贡舶贸易”,是指宋代以后中国政府准许外国使节在进贡的前提下,随所乘船舶、车马携带商货来中国进行的贸易。
到了清代,广东产品的出口进一步繁盛,广东本地市场对外省以至外国商品的需求也大大增长起来。甚至有“就粤而论,藉外来洋船以资生计者,约计数十万人”这样的说法。
此时,广东地区各级市场与外贸市场之间已经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形成了一个以出口贸易为导向的市场体系。乘着出口贸易不断发展的东风,广州城内的商品琳琅满目,店铺林立。走木巷、麻行街、象牙巷、孚通街、绒线巷、扁凳巷……一条条具有浓郁商贸特色的古老街巷紧贴广州城南水路,相连长达十数里。
如此繁盛的商贸发展背景下,自然会有很多充满商机的新兴行业在广州这片贸易中心的土地上应运而生。而这些新行业的出现,促使广州手工艺一步步走向封建社会时期的黄金时代。接下来,就让黄海妍馆长继续为我们介绍这些吸引无数外国商人疯狂买买买的广州手工艺品吧。
黄海妍馆长按照这些手工艺新行业的演变过程,将它们分成了三大类。其中,源自于本地的手工艺品当中,就以广作家具为主。
由于广东是贵重木材的主要产地之一,南洋各国的优质木材也多经由广州进口,使得制作家具的原材料比较充裕。据黄海妍馆长介绍,这些优质的木材会运送到玉带濠南北两岸的家具作坊,经过“开料”、“抖榫”、“鑿花”、“刮磨”、“上漆”等工序之后,才制成可以进行出口的广作家具。
广作家具同时也是进贡朝廷的贡品,在两广总督李侍尧恭祝乾隆皇帝61岁寿辰的贡品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份清单:“紫檀雕花宝座壹尊、紫檀雕花御案壹张、紫檀镶玻璃三屏风壹座、紫檀雕花炕几壹对、紫檀雕花宝椅拾贰张、紫檀雕云龙大柜壹对、紫檀镶玻璃衣镜壹对、紫檀雕花大案壹对、紫檀雕花天香几壹对……”当中出现了多款紫檀雕花家具,足以说明广作家具深受皇帝的喜爱。
而源自中原地区、但得以在广州得到孕育和发展的手工艺,就不得不提广彩瓷。
明末清初,海外市场对中国瓷器有大量的需求,结合广州港的出口贸易条件,广州商人改变了以往的贸易做法。他们不再从瓷器名都景德镇购买瓷器成品,而是只在景德镇买进价格低廉的素白瓷胎半成品,再把景德镇的绘彩工匠请到广州工作和授艺,并在广州城西开炉烘烧彩瓷。
为了让产品更加符合出口贸易市场的需求,绘彩工匠在继承中国彩瓷传统的基础上,融入了西洋的画法加以彩绘,广彩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渐渐兴起。
民国时期,广东梅县人刘子芬就在《竹园陶说》中这样记载:海通之初,西商之来中国者,先至澳门,后则径越广州。清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埠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
到了清代乾隆嘉庆时期,广彩仿照中国缎锦纹样作为瓷器装饰,并称为织地,后来更是用金水织地,形成了近代广彩“织金彩瓷”的特点。
除此以外,广彩还灵活引进了外国的西洋红、鹤春色、麻色、茄色、粉绿等特殊颜料,逐渐形成了“堆金织玉”的独特风格。
既吸收了传统的中国手工艺技术,也吸收了西洋地区的艺术精华,就像广府地区特有的海洋文化一样,广彩也在坚守传统和持续创新当中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
清同治至光绪年间,广彩的繁盛更是达到了顶峰。据说,当时加入广彩行会组织“灵思堂”的人数就已达三千多人。
在当时广州新兴手工艺行业中,还有一些是源自欧洲的。
刚才我们也提到,在广彩形成独立风格的时期,广州工匠不断吸收西方的艺术精华。在这个过程中,也促使了他们学习并掌握进口的欧洲工艺技术,由模仿到创造,充实并丰富了本地传统工艺美术。由此形成的广州画珐琅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
康熙年间两广总督杨琳曾在奏折中写道:“本年五月十二日,到有法兰西洋船一只,内有法兰西行医外科一名安泰,又会烧珐琅技艺一名陈忠信,奴才业会同巡抚公折奏闻,于六月十八日,遣人伴送赴京在案……”。
乘搭陈忠信的法兰西洋船首先到达的就是广州,可以推断,在广州开海禁之后,像陈忠信这样懂得画珐琅技艺的传教士最初抵达的地点也是广州,他们不仅带来了西方的画珐琅,也带来了画珐琅技艺,并传授给广州的工匠。
广州从康熙五十五年起,就成为内廷珐琅作的技术人员和珐琅材料的主要来源地,也是画珐琅器的供应基地。
广州画珐琅的需求量不断增大,不仅要满足本地、各省和皇家的需求,还要在本地为外商进行加工制作,甚至有工匠受邀漂洋过海至外国制造画珐琅。
随着大量的中国丝绸、瓷器通过广州出口至欧洲,不少中国人的生活用品和手工艺品也随之西传,这些生活用品和手工艺品很快就演变成为当时欧洲家居陈设中的时尚物品,并在欧洲上流社会中掀起了一股崇尚中国艺术的“中国风”。
在“中国风”的影响下,广州的工匠批量生产为欧洲市场定制的瓷器、漆器、纺织品、扇子、雕刻等外销艺术品,源源不断销往欧美。这种现象在18世纪70-80年代达到了鼎盛,广州的手工艺也因此进入了闻名世界的黄金时代。
接下来,黄海妍馆长以外销工艺扇为例,向我们介绍广州手工艺对欧洲装饰工艺的影响。
这是由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收藏的外销工艺扇。在当时的外销工艺品当中,肖像、人物、风景、静物与历史神话、宗教画等均是常见的纹饰题材。这把扇子通体镂空雕刻并以垂直牙丝补地,上有三个椭圆形开光,开光正面是油画绘“耶稣降生”图,反面为水彩绘花卉图。边骨深雕菊花枝叶纹与亭台楼阁纹相间,是乾隆年间象牙折扇的特征。全扇具有典型的外销品特色,工艺十分精湛。
而这一把由扇子博物馆收藏的工艺扇,它的镂空雕刻象牙扇骨为中国工匠制造,扇骨正中开光采用了垂直牙丝补地工艺,边骨则为深雕亭台楼阁,体现了典型的广州外销扇特点。扇面是英式风格,有新古典主义的纹饰,中央圆章内为经典的“普林尼的《鸽子》”图案,左右则是罗马建筑——左侧为火灶神维斯塔的神庙,右侧为医者密涅瓦的神庙。
(华丽的分割线)
除了制扇技术的融合以外,扇面上选择的题材和纹饰也常常能够让我们看到中西文化元素的交织。
以这一把由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的彩绘纸面折扇为例,折扇本身虽然是由英国制造,但扇面融合了西方古典风格与“中国风”。扇面正面有一位在风景中弹奏里拉琴的西方古典女性,可能是缪斯或是歌舞女神特耳西科瑞。她的肩头靠着陪伴她的丘比特。
扇子反面的“中国风”画面当能取悦彼时法兰西持扇之人:但见正中开光里描绘了一个年轻女子与其情人私奔,两旁开光里还有演奏乐器以及选用条带与丝绸梳妆的女人。彼时的法国艺术流行私奔和梳妆题材,诸如弗拉戈纳、布歇等艺术家都有绘画创作。在这把扇子当中,这些题材却是采用中国风格进行表现。
(华丽的分割线)
从以上几个鲜明的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广彩的形成、广州画珐琅的出现,还是外销工艺扇的中西文化结合,都与广州手工艺工匠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才华、主动吸收西方艺术精华息息相关。
广府地区具备对外贸易的优越条件,形成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工匠们同样具有这种文化中鲜明的开放性、包容性、创新性、灵活性,在坚守广府传统工艺的同时,主动创新,主动作为,结合国内外用户需求和时代要求,为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和创意!这也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在今天传承和弘扬,守正创新,为传统工艺找到突围之路。
黄海妍馆长为我们介绍的广州手工艺又岂止这些,如果想要欣赏更多美轮美奂的工艺品,就快点扫描下方的二维码观看本期讲座吧!

欢迎转发,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公益讲座资源!